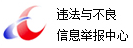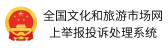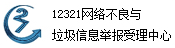何成结:相伴终生是为缘——黄梅戏基层工作者何成结的从艺小记
何
成
结
1951年农历七月初三子夜时分,我出生在怀宁县石牌下街东南方向莲花塘畔陈家祠堂内的一处偏屋里。
陈家祠堂在怀宁县大名鼎鼎,1938年就由石牌政界、商界头面人物联合改建成一座正规戏院,徽戏、黄梅戏艺人均在此演出献艺。这座简陋的由祭祀大厅改建的简易舞台,不知走过了多少名伶好佬,不知有多少观众在这里流连忘返。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这块风水宝地划拨给以黄梅戏艺人为主体组建的怀宁剧院,几十号艺人一起在这里生活、工作。一年365天,天天是白天排戏,晚上演出,弦索不断,锣鼓铿锵,伴随着我蹒跚学步、呀呀学语的童稚期。可以说,我的胎教和童趣就是浸润在这种怀腔的声韵之中。
模糊的记忆中,跟着小伙伴在莲花塘钓鱼,在大广场上看露天电影,在石牌新剧场建造的工地上刨花堆里玩耍,每当这些碎片化景象在脑海深处浮现,总有陈家祠堂每天例行的闹台锣鼓声响相伴闪回,儿时的成长过程,似乎与黄梅戏音乐的节奏同步,此情此景,刻骨铭心。
1957年4月5日,在记忆中较为鲜明,一大早,我跟着怀宁剧院的大人们,来到新落成的剧场门外,在摄影师的指挥下,列成几排,6岁的我坐在年轻演员张亭腿上,拍下了这张全团演职人员的合影照片。这是1957年全团人最为齐全的一张合影,十分珍贵。合影后大家把我一家送至猫山车站,乘车赴安庆新成立的安庆专区黄梅戏剧团报到,团址在安庆师范大学红楼东侧操场旁的两排小平房内,当时属海军学校,操场上还有许多海军专有的训练器械。红楼西侧有一个小礼堂,是剧团排戏之所,首演大型历史剧《黄金印》就在这里排演成型的。每天的演出,我都跟着妈妈步行出师院,过马路上城墙,路过城墙上雷达防区,进锡麟街转孝肃路,到达吴越街的民众剧场,晚上在后台玩乏了就睡在大衣箱上。1958年的春节就在师院的剧团驻地过的,只记得左邻右舍的老艺人左四和、龙昆玉、李普唐等爷爷都给了我几角钱的压岁钱,欢乐得不得了。记忆中忽然有一天,全团人背包提篮,集体搬迁到孝肃路天主堂对门的一处很大的西式建筑楼院中,当时都称其为嬷嬷院,这个新的剧团驻地就是相伴安庆专区黄梅戏剧团发展成长的中兴之地,大名鼎鼎的锡麟街31号。
对于锡麟街31号,几十年住客前后数百人,可能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座精美的建筑群了,这里每个房间,哪一处天花有灰泥脱落,哪一处木地板有不平翘起,院中冬青树上有几处蜂窝,阴沟上的石板哪一块有铜矿析出,我一个8岁孩子整日在这里盘桓穷游,只记得这里天天都很美好、祥和,从上小学到进初中直至被卷入文化大革命,我的家都住在这所院落里。
锡麟街31号既是百十位演职人员的生活场所,也是其艺术训练和创作之地,每天在院中的练功,在排练厅中的排戏,像王鲁民、麻彩楼、王兆乾、杨琦等当时已享有盛名的大师们给年轻演员说戏,解析真的是精彩、高级。小小年纪无所事事的我常常侧立旁听,虽茫然不懂,但久听必有一点所悟,这种艺术启蒙令我受益终生,历历往事刻骨铭心。由我撰写并出版发行的《锡麟街31号》就是我自1958—1968年在这所院落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
在黄梅戏文化的浸润下,我从孩童成长为一个初中毕业的青少年,1968年11月作为老三届上山下乡,下放到枞阳县陈湖区花园公社,成为一名知识青年。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一下子就把我从戏曲虚拟的美好环境中拉扯到严峻的现实之中。自此,挑担、车水、插秧、割稻是必学的技艺,必须承担的工作责任。随着父母作为下放干部也搬出锡麟街31号回到原籍农村,仅存的一点戏曲情结在脑海中渐渐散去了。
艰辛的劳动,良好的表现使我不到两年就被推荐招工到安庆机床厂工作,成为一名钣金放样工。工作生活的环境好转,我是十分珍惜的。于是我努力学习,发奋工作,在同工龄学员中,技术提升得算是很突出的,有两年农村劳动磨炼出的耐力和韧性,所以在工厂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一点不觉得劳累,这种快乐和认真的工作态度深得车间师傅们的认同与赞赏。1972年4月,得逢机遇,我被推荐至合肥工业大学机械系热处理专业学习,成为了特殊年代的一名光荣的工农兵大学生。
在合工大三年的学习收获是巨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份感触就越益强烈,特别是一个单纯的青年工人。在那样高端的知识平台,在那样深入浅出的理论学习中,在一大群良师益友的帮助、影响下,思想认知的提升,科学理念的进步,全部完成于无形之中,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理解与价值取向的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特殊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绝大多数都成为了优秀的、兢兢业业的基层劳动者中的中坚力量,这是绝对值得尊敬和肯定的。
文化动乱,上山下乡,招工进厂,上大学学习,十几年中工作繁重,生活艰辛,为成家立业忙碌得焦头烂额,心灵深处的戏曲情节,生活中的艺术节奏,早已消失在爪哇之国。恰好那个特殊的年代也没有什么戏曲可看,这门艺术的影响力在心灵深处越来越远,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文艺的春天终天到来,我所居住的皖江影剧院,天天都有戏剧演出,熟悉的声腔、熟悉的故事、熟悉的舞台节奏,尘封已久的戏曲基因一下子被激活起来,自幼养成的戏曲亲近感渐渐地满血复活。那个时段,我几乎天天看戏,随着戏曲的旋律,开始琢磨、思考。十多年的工作,生活磨砺帮助我的认知能向更深层次去开掘和探索,人生中的所有积累都是有益和有用的。因为我深深理解,一个思想家不一定是艺术家,而艺术家必须是成熟的思想家。我在工厂与农村的深度介入和切身经历,对我思想认知的提高和后来从事编剧职业的帮助作用是巨大的。
1978年,我结婚、生子,生活完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状态。
1981年,我已入而立之年,在安庆市机床厂热处理车间任技术员。日复一日,按部就班地重复劳动,思想上是非常清闲自由的,且正是精力旺盛之年,每天剧场里传来的锣鼓弦乐又拨动着我心灵深处的戏曲情结和思维。爱子何培时已三岁,晚上八、九点钟,孩子入睡,我不能走远,坐在孩子摇床旁的书桌前,但思绪可以奔腾得很远很远,总想着在休息前这两个多小时可以干点什么。几度权衡后,决定创作一出大型的黄梅戏剧本。一为活得充实,二为分散使用不完的精力,三为这两小时我本来就是要在孩子摇床边照看,写剧本、看孩子两不耽误。于是,在皖江影剧院一间狭小的平房内,一盏昏暗的自制台灯下,开启了我的戏曲创作之路。
构思一出戏,比其他艺术门类的构思,可能要困难一些。因为它要受舞台空间、时间、表演等等方面的制约。开始我想借鉴一些历史演义、今古传奇,找一些现成的故事改编。翻了一些书,但发现有些可以成戏的早已被人搬上舞台了,有些又不适宜写戏。我为此仿徨苦恼。后来我想找不到现成的,就自己慢慢编一个吧,这样还不会撞车,自己感受挺深的东西写出来或许会更深刻一些。我在读历史故事时,好坏忠奸的官吏对国家和人民所起的治废兴亡的作用,常使我嗟叹;在我短短的生活历程中,更经历了“四人帮”篡据高位,给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十年动乱。古人把国家比为大厦,官员比做栋梁。栋梁腐朽,大厦即倾,赖大厦以庇护的人民就要遭殃了。由这条思路,我构思了随着一名地方官吏的升迁,忠与奸之间的一场斗争,这样,一出古代公案正剧的雏形就出来了。
得益于自幼在老专团里的耳濡目染,无数次地听杨琦、王鲁明、王兆乾等大家的讲戏析理,这种扎实的“幼功”真的不可小觑。对一出大戏的起承转合,人物的刻画塑造、情节的设计安排,我创作得十分流畅顺利,只用了二十多个晚上,七场黄梅戏《血染袍红》就全部完成了,与黄梅戏十年分离,自此时起算得再续前缘了。
在我的处女作《血染袍红》剧经安庆地区黄梅戏剧团公演后,报纸报道、电台采访,已经引起安庆市文化局汪存顺局长的关注。他派人事干部来工厂和我联系,希望我调进市文化局从事专职编剧。思考再三,我还是婉拒了汪局长的好意。原因有二,一是自忖才疏学浅,业余创作可能冒尖,专业编剧自己并非科班,底子不足,可能会末流垫底,心有不甘。二来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刚刚启动,全国上下,政通人和,万众一心,各行各业都是兴旺发达之势,当时的机关和企业几乎没什么待遇上的差别。我当时的工资是74元,每月还有浮动奖金6元,工种营养费9元,若调入机关工作,一月要少收入近16元,在当时级差只有5元的情况下,工资等于是连降三级,这样的现实问题,容不得我不作慎重的选择。
1984年8月,安庆地区文化局局长方博闻来皖江影剧院检查工作,顺便找到我,谈起能否调入戏曲创作室工作的事情。由于我的父母在地区文化部门工作几十年,我自幼便认识方博闻局长,所以说起来宽松、方便了很多。当方局长了解我一直借住皖江影剧院时,当即允诺会第一批考虑解决我的住房问题。这样的优厚条件,令我顿生感激。能摆脱多年寄人篱下之困,我还能犹豫什么,1984年10月,办好一切手续后,我正式进入安庆地区文化局上班工作。
从19岁进厂当学徒,历经上大学,当技术员,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一年四季50多度的热处理车间高温,整整15年的产业工人,辛苦劳作,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儿时和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和成长环境之中,人生轨迹真的如梦似幻。
安庆地区戏剧创作室既是黄梅戏舞台剧本专业创作单位,又是指导全区专业、业余剧作者的业务指导机构。当时创作室主任是田耕勤,副主任为程久钰,创作员是吴朝友和我两人。1988年,安庆地、市合并,与市创研室合并重组的创作室人才济济,实力强大,领导班子由书记田砚农、主任田耕勤、副主任魏启平、程久钰组成,创作员有王秋贵、石楠、黄义士、吴朝友、何成结、都咏梅、郑跃春、周韵琴等中青年编剧,全地区8县还拥有17名专业、业余的剧本创作人员,创作力量领冠全省,每年的全省新创剧目研讨会上,安庆的作者、作品一定是绝对的主流。戏剧界神往的“出人、出戏”景况在当年原本是寻常之事,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剧作者们每当忆及莫不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上世纪80年代初,解放思想的步伐渐渐加快,全社会都在反思审视,在戏剧界中,这个时段对各种题材的涉猎可谓是百花齐放,其中不乏出现了大量解构社会剖析人性的传世作品。所有文学艺术门类的工作者,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鲜有置身事外的。
与其它科班出身的编剧不同,两年的农村劳动和15年的工厂生活使我观察生活和提炼素材的角度总是有些特立独行。
1985年,我创作了大型古装戏剧《人狐》。
十年动乱期间, 耳闻目睹了很多人间丑恶, 亲人反目、师生相残、人性的卑劣,重创了整个社会,籍此思路结构了一个集爱恨情仇的传奇故事,写出一部大戏,解析人性中的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说明原始的兽性在人性中是有遗传存在的。如狼性的凶残、狐性的邪恶,这些反人类的恶性在社会条件发生病变之时就会释放出来,进一步破坏人类的天性与道义。因此,构建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体系才能抑制这种兽性病毒。因为剧中反面人物阴狠狡诈、充满狐性,所以剧名定为《人狐》。
《人狐》剧本1987年由湖北《乡土戏剧》第三期发表,1988年安庆市黄梅戏三团决定投排,导演、音乐、主演都已确定见面。因当年底安庆地、市合并,所有单位格局同步进行重组调整的大事耽搁下来,到了1989年,原定的排演计划彻底地歇菜没戏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然成就巨大,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国家和人民都明显地富起来了。文化艺术事业更是欣欣向荣,生机勃勃,更多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表演及声光技艺都被引进戏曲舞台之中。的确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
在如此大好形势下,作为基层戏曲创作人员的我,强烈的创作冲动是自然发生的。多年的职业创作养成了“逆向思维”的习惯,根据已被公开处理的官场腐败案例,写出故事、人物上的设计和主题上的定性,以半个月的时间创作出公案大戏《桃李无言》。
《桃李无言》是一部揭示恶劣社会制度弊端的作品,它指出抑善扬恶是官场贪腐的根本源头,其立意上的尖锐和言词上的辛辣在黄梅戏以往的舞台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动笔之前,我也曾踌躇再三,当在一次闲谈中,时任安庆市黄梅戏三团业务团长朱茂松得知我有此创作计划,立即连连叫好,鼓励我一定要写出来。在他引荐该团的主要领导杨长江和阚根华并得到他们一致认定后,我开始了剧本创作,完稿后交付。这部戏于1998年投排并公演,由当时团内著名花旦演员孙娟领衔主演。在当时戏剧市场已呈滑坡态势的大背景下,演出十多场却场场爆满,观众真的是很喜欢的。这部讽刺意味强烈的传奇正剧具有较强的喜剧效果,好看且好玩,认真去想也有一些深刻的东西。
1998年的一天晚上,省里主要领导来安庆视察,招待演出的剧目就是新剧《桃李无言》。观罢后,省领导倒未说什么,陪同观看的市领导大发雷霆,把剧团领导训斥一顿,大吼说为什么让我们看这样的戏?似乎是剧中对官场腐败的揭露太狠,讽刺得太过。这位市领导并不腐败,退休也是平安着陆,真的很不理解他为什么如此反感这出戏,难道这就是“看得说不得”的危险题材。进入新世纪后,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又排演了此戏,只是作为“吃饭戏”进行日常演出,招待领导、节庆活动再也没有参与了。几十年过去,现在想想说说也很好玩的。当年的少年心态,狂妄随性,不知天高地厚,幸运的是所处是极好的年代,若逢以言招祸之时,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批判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批判型思维,使我在选材和创作上总显得很沉重,几十部大小剧目能够聊以自慰的也就是无一部有跟风吹捧的痕迹,作品水平和成就处于不黑也不红的中下游状态。时逢戏曲市场逐渐滑坡的态势,剧本的需求萎缩严重,我与众多的同行都停顿观望起来,追求与现实渐行渐远真的令人难受,但确实也无可奈何。

2001年一纸调令,把我从迷惘、徘徊的境遇中解脱出来,我被调动任命为《黄梅戏艺术》编辑部主任。主编这本已创下赫赫大名的唯一国内外公开发行的黄梅戏刊物。知天命之年,能够得到提拔与重用,升上一个小官,改了一个大行。春风得意之际,不乏雄心勃勃,对刊物和自己的未来完全是一片光明的憧憬与预期。
《黄梅戏艺术》创刊于1981年,两位主编王兆乾、黄旭初都是学养深厚、艺术经历多彩的饱学之士,他们前后二十年的苦心耕耘,把这份地方自办的小型刊物打造建设成名扬全国发行海内外的艺术期刊品牌。个中甘苦,我在接任后,方能有了刻骨铭心的认知与体会,黄梅戏各行各业的前辈先贤,真的需要隆重和真诚地致敬致谢的。
我出身梨园世家,对戏曲认知、舞台空间的掌控自诩了如指掌,黄梅戏发展历史,表、导、演实践与理论也是多有涉猎,大的门径是基本知晓的。主编一本刊物不说绰绰有余,努力一下能够得心应手我还是自信满满的。
进入岗位后,主编的第一期刊物就让我感到焦头烂额,力不从心,“隔行如隔山”、“书到用时方恨少”两句俗语几乎天天在我的编辑实践中反复出现,作为职业编剧,需要以形象思维去思想,去创作剧本,而作为刊物编辑,审读各家各派的理论文章,就需要依从缜密的逻辑思维去研判、分析。对于黄梅戏发展历史和艺术理论,我一直认为了解很多,谈起来也能头头是道,写起来也能创一家之言,但读稿越多、涉猎越广,越觉自己真的浅薄无知。黄梅戏从乡村草台唱进城市,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崛起,直至今日跻身中国五大剧种行列,历时数百年的演变与发展,历史与理论哪一段都有博大精深之处。作为一个刊物主编,必须具有真诚的敬畏之心,尊重真实的历史,尊重各人的观点,拾遗补缺,挖掘研究,这样刊物的价值方能充分体现。
从2001年入职到2011年退休,我在《黄梅戏艺术》主编任上整整工作了十年。度过了第一年手忙脚乱的学习编辑过程,在同事王倩、邓新生的帮助下,我渐渐地熟悉和轻松起来,在亲手建立稳定的作者群和读者群之后,编辑工作自然地按部就班和有条不紊地运行,开始有时间、有精力去发现和开拓一些有益于黄梅戏创作研究的学术课题,生活、工作顿显充实和有滋味起来。
黄梅戏是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后高速发展和迅速崛起的地方剧种,在出人出戏方面,成就非凡,十分突出。但在大步前进的过程中,对剧种发展史实、音乐基因的梳理,文化理论的确立等方面,多有疏漏和不足乃至缺失之处。进入新千年后,随着党和政府对黄梅戏艺术的关怀和投入不断加大,随着黄梅戏业界同仁的自尊自重和同心同德,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在安庆地区日渐繁盛,作为专业期刊的《黄梅戏艺术》承担重任自然是责无旁贷。我作为这个时间段的刊物主编,自是缘分使然,上下求索,十年劲头不减,虽教训多于成就,苦涩多于甘甜,甚至常遇好心无有好报之尴尬,奈何前缘早定,真心无悔,快乐始终地体验着“爱拼才会赢”。
2001年12月,《黄梅戏艺术》期刊联合安徽省黄梅戏艺术发展基金会,接手召开安徽省文化厅每年例行召开的剧本创作研讨会。作者涵盖安徽、湖北、江西、江苏四省,至2021年已连续召开20届,培养和建设了一个强大的作者群体,在剧本创作和理论建设上获益匪浅。
2005年10月和2007年5月,两次组织专业团队,赴湖北、江西有关市县农村,调研采风,开启了黄梅戏起源历史寻根探源的学术之旅。
2007年5月,策划并主持录制百段经典黄梅戏唱腔专辑《寻找湮逝的黄梅》,对黄梅戏音乐的起源、形成进行了实证上的梳理和确认。
2008年6月,策划并参与将传统黄梅戏剧目三十六本大戏以连环画的形式记录下来,并以“黄梅戏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的方式出版发行。
2009年3月,参与策划并担任艺术顾问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大戏黄梅》的拍摄工作。该片于同年摄制完成,作为当年中央电视台精品节目之一,国内外公开发行播映。
光阴飞逝,留下了这些流水细帐,记述了我这样一个并非科班出身的基层戏曲工作者,以半路出家的方式进入黄梅戏艺术事业,在文化盛世的大环境中工作经历,我知足、感恩,以生平爱好作为终身本来就是大幸之事,能留下这些聊以自慰的艺术足迹,略报知遇之恩,更是望外之喜了。所以记此,以证相伴终生是为缘。